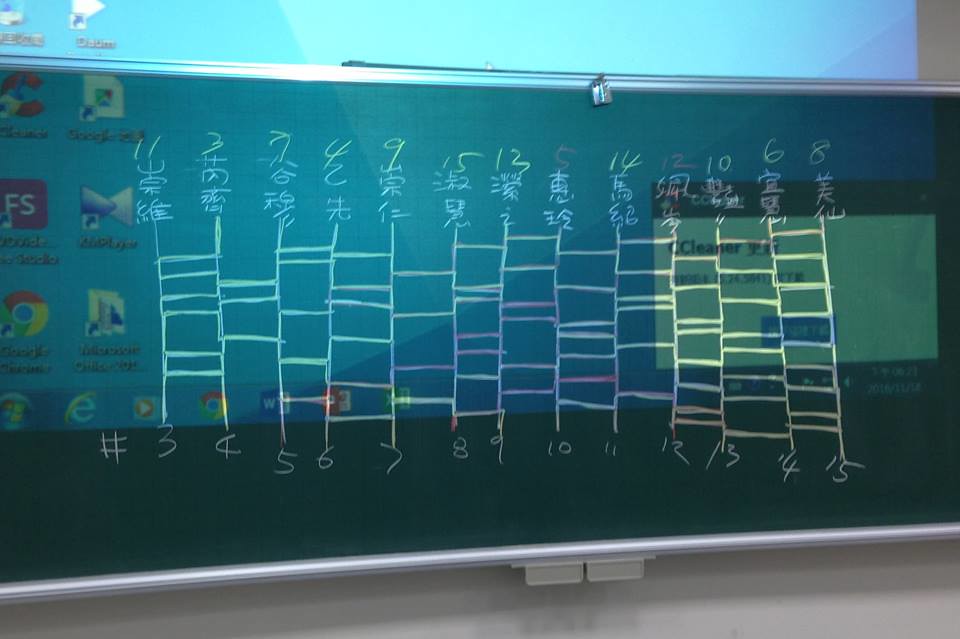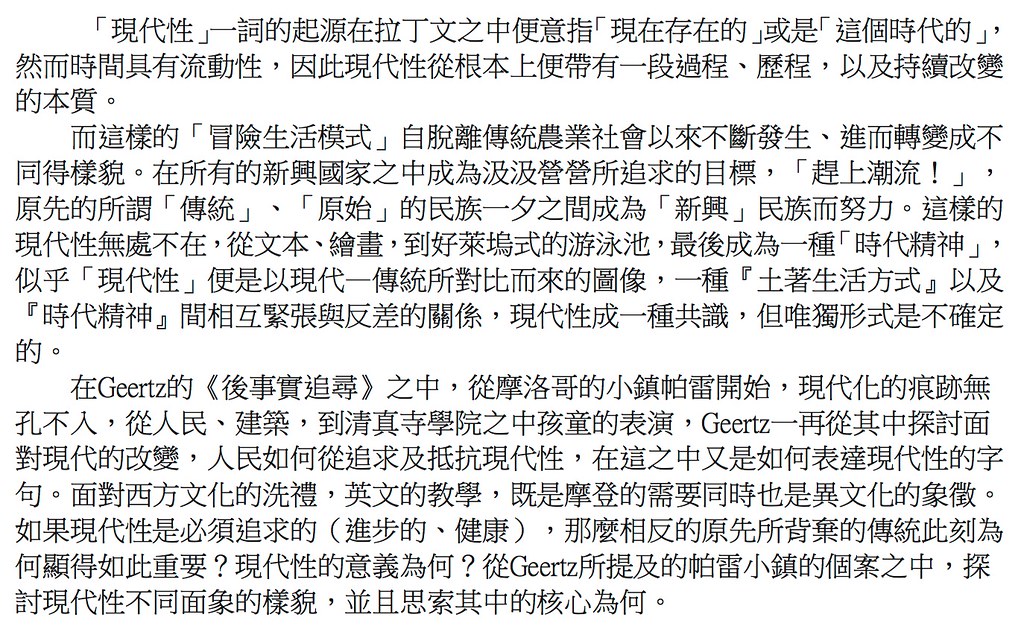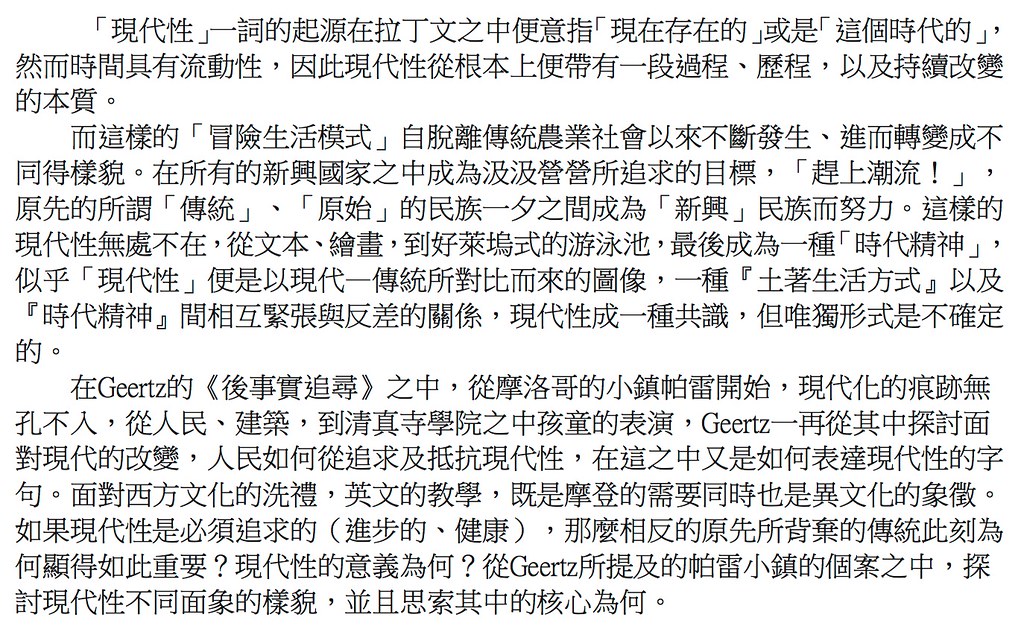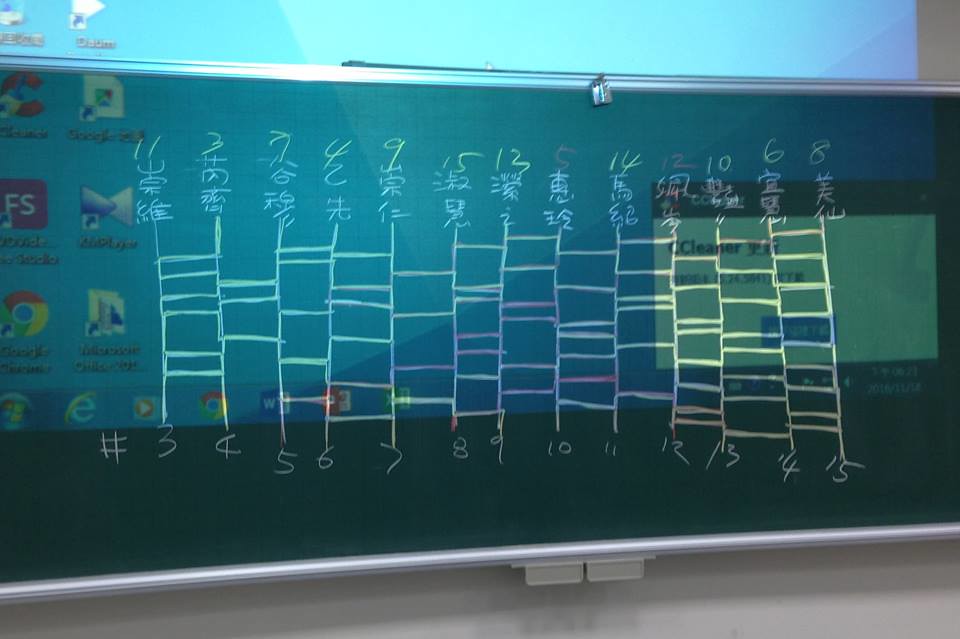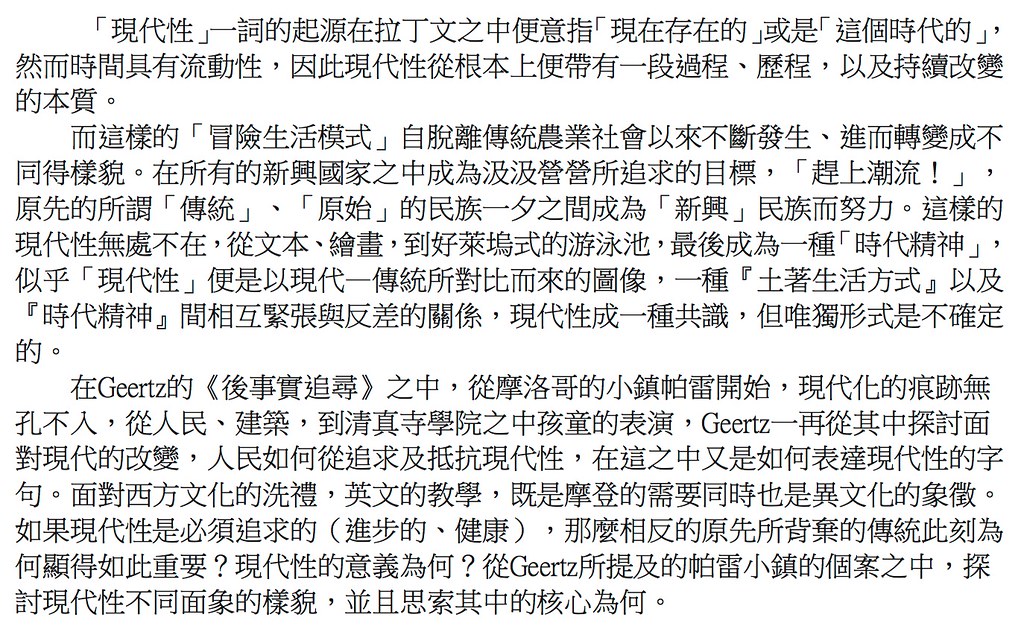本週五課程:Available Lights,簡體版翻譯為「燭幽之光」,或是過往學長姐翻譯成「未盡事宜」。
這週我們會聚焦在「異質性並存」主題。照例,請同學留下閱讀心得。
備註:12月2日當週,請同學準備500字的期末作業題目描述(限這學期讀本內容,先別離題應用太遠)。不講課,我聽同學們報告。別忘了,這門課就是帶領各位如何提問;避免定義式的蠢問題。請參考歷屆「文化理論」博士資格考題,例如:
1. George Marcus在〈The Uses of Complicity〉文章裡評述過往人類學調查過程中——即便充滿困難恐懼、不確定、偶發事件,或是涉及倫理處境、自我懷疑——與研究對象建立起和諧一致的關係(rapport),始終是民族誌田野工作的門檻與成就標誌,依此彰顯外部者得以平和地進入內部者的世界(Ethnography through Thick and Thin, 1998:106)。然而人類學處境始終充滿合作、矛盾與衝突,於是人類學家與研究對象的「同謀」關係(complicity)——作為雙方對待彼此的互存狀態——表達了一項在田野調查時所面臨的「人類學諷刺」(anthropological irony; Marcus 1998:110)。這種民族誌書寫者的自我覺察意識和倫理姿態使得人類學逐漸反省究竟「我們」是誰:例如Johannes Fabian在Time and the Other(1983:157)宣稱「The We of anthropology then remains an exclusive We [略]」、Clifford Geertz在Works and Lives指陳「Who are we to describe them? 」(1988:135)、Akhil Gupta和James Ferguson在Culture, Power, Place(1997:24, 42-44)則強調「How can “we” anthropologists presumes to speak for “them,” our informants? [中間略] Who is this “we”?」請評論當代民族誌知識生產之「人類學諷刺」為何,並依據上述文獻回答「那麼,『我們』究竟是誰?」
2. Clifford Geertz在論述「人類學本質」時,堅稱「每個嘗試過的人類學家都知道,困難在於幾乎不可能去傳達這門學科的本質究竟為何,或甚至它的根源所在。 [⋯⋯] 我們缺少語言來說明,當我們在工作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似乎有一種文類消失不見了。」Geertz並且以某部電影中的口述情境說明此一「消失的文類」:「『小超人被困在帳篷中,他身邊只有圍成一圈的印第安人。大草原上已經升起了火,他沒有多餘的子彈,食物已經盡數吃完,夜幕降臨。小超人該如何逃出帳篷?第二十二章結束。』停頓一下,史肯頓整理了思緒,接著他說:『第二十三章。在小超人離開帳篷之後⋯⋯』」(《後事實追尋》中譯本,2009:162-4)。請申論Geertz認為的「消失的文類」指的是什麼?Geertz以個人經驗所提出的觀點為何?以及1980年代之後,詮釋人類學追隨者的主張又是什麼?
3. Clifford Geertz在〈宗教作為文化體系〉一章中表示「我們上演一齣沒有王子的《哈姆雷特》已經很久了」(1973:109),請詮釋其意;同時綜合闡釋Geertz其他論述(1973, 1983),如何透過「象徵符號」得以完成「文化體系」概念?並且解釋何以晚期Geertz於2002年受訪中澄清「我不研究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