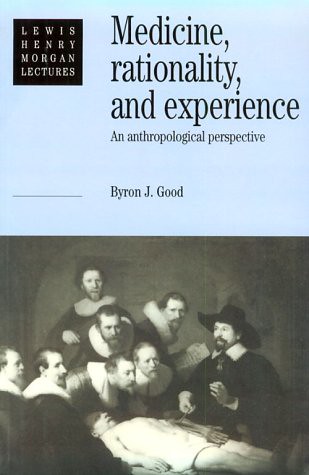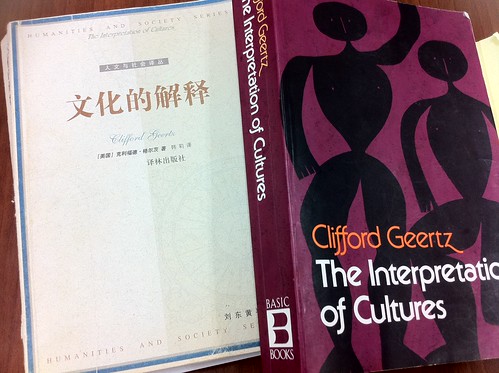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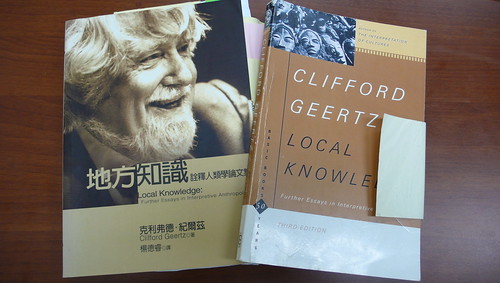
◎Micheelsen, Arun. 2002. “‘I don’t do systems.’ An interview with Clifford Geertz,” in Method & Theory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 (14)1:2-20.
◎Joseph Errington. 2011. “On Not Doing Systems,” in Interpreting Clifford Geertz.
★Clifford Geertz
1. Religion as a Cultural System (1973)
2. Ideology as a Cultural System (1973)
3. Common Sense as a Cultural System (1983)
4. Art as a Cultural System (1983)
以一種綜合理解(卻因此不得不聚縮其論述組織而感到不安)的閱讀經驗看來,葛茲主張文化猶似一個具備象徵符號和意義的秩序體系,使得人們在其中詮釋他們自身的經驗。葛茲在早期論述中,將宗教、意識形態、普通常識、藝術等視為一項文化體系,此一語法承襲帕森斯的社會行動結構,但不同於純然將文化體系作為研究者建構論述之手段或媒介——「我不研究體系」晚期葛茲如是澄清——葛茲視文化體系為研究者調查分析的尋獲,以突顯文化內部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並非依賴於文化體系或組織內部之間澈底的連結,或是彼此高度整合協調,致使全體大規模地共同行動,卻反倒像章魚一般,「各個部分散開各自行動,但整體累積下來卻是朝固定方向移動」。
稍稍再加以精確地說,在1973年的宗教與意識型態作為文化體系兩篇論文中,葛茲顯然用盡全力試圖鋪陳兩項主題:一是建立以「詮釋」(的人類學)作為探求(文化的)「意義」的手段,藉此樹立詮釋人類學的核心主軸;二是對人類學思想中有關「世界觀」的論述。
這兩篇1973年文章都涉及對宗教的人類學式理解(別忘了,葛茲的博論主題便是宗教;《文化的詮釋》中接續「宗教作為一種文化體系」的下一章ethos也談論宗教)。前者「宗教」以model of和model for(簡體版翻譯為「屬於」和「為了」,我則歸納為「程度」與「指向」)兩種模式,使得「宗教行為vs經驗性」變成是一項具備「意義」的行為(這也呼應葛茲的論點「意義是尋獲的,不是與生俱來的」)。相對來說,後者則是就事物現象透過「意識型態vs科學」的辯證方式。這其中,「意義」在「宗教」這章透過符號、特徵、概念、定位,在「意識型態」這章則透過語意學(有時候,葛茲用「符號模型」這種說法),進而理解世界觀和人生觀。這兩章都帶來了一些挑戰;就我的說法,這種挑戰使得人們進入一種「混亂」之中,例如「受難」是一個例子。
1983年的常識與藝術作為一項文化體系兩篇論文則相對較為易讀。兩章不再是以「提出一種新觀點」的語調,而是就既有已被接受的思考方式提出相對較不激烈的論述內容。在這兩章的核心概念裡,將「常識」與「藝術」視作文化的「縮影」,恐怕有助於閱讀:前者葛茲提出「作為研究主題的文化被漸進地鋪陳出文化的形貌,與作為日常生活的文化其浮光掠影的形貌,二者有何差別?」(也就是詢問:「常識」是什麼?」「常識是一項文化體系」,因而帶來了某種「秩序」→讓我們再想想1973年這兩章所企圖帶來的「混亂」);後者葛茲則是主張:「藝術的創作,與創作時對於生命的感受是不可分割的」(「在這種感性之中,事物的意義就是人類蝕刻在事物上的刀痕」←這種主張和梅洛龐帝認為「世界是透過身體向我們開展」是相似的邏輯的),就我的說法,藝術的諸多符號,正因為是安置在它的文化之上才帶來對於生命的強度(讓人無以名狀地受到感動、讓人收穫到一種奇特的力量)。於是符號學必須超越符號解碼的層次,而是一種思維,一種等待被詮釋的語彙,一種診斷學;由此,古蘭經詩人的演出,或是naven中在集體會社中的嘲諷式論辯,方可開展一種關於生命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