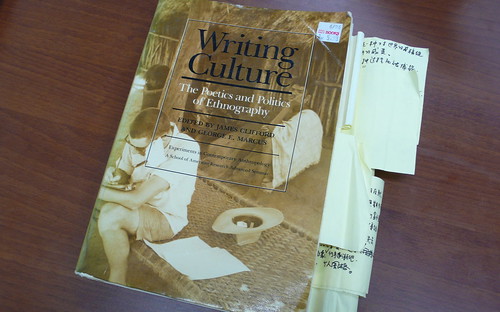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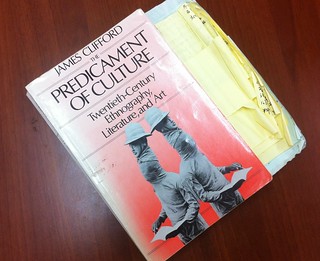

Partial truths
◎Literature --> metaphoric/allegorical (rather than observed facts).
de Certeau --> fiction (lacking "univocity")
literature and fiction are fundamentally unstable. It always narrates one thing in order to tell something else.
◎ethnographic fiction --> loses its connotations of falsehood which opposed to truth.
it is something made or fashioned to preserved the meaning not merely of making, but also of making up, of inventing things not actually real.
--> true fiction: selected and imposed meanings as cultural translations.
--> ethnographic truths are inherently partial committed and incomplete. (it is related to power, rhetoric, and gender, for example.)
Self-reflexivity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draws attention not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texts but to their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author is separated from the objective refrent of the text.
--> but how was its "objectivity" textually constructed? (Then a sub-genre, in terms of "self-reflexive fieldwork account" emerged.
--> the ethnographers, a character in a fiction, therefore is at the center stage.
authority
◎informants become co-author.
"We"--> requires historical identification. (in comparison to Auge, Fabian, Rabinow, and Geertz).
5 則留言:
當我們說:「眼見為憑」時,我們以為在場看見為真。但是之前的與這周的閱讀,告訴了我們,即便在場的見證,那也只是「我以為並相信的真實」,但不是全部的事實(誰能說出全部呢?)。而事後的敘說更是一種建構「我相信的事實」的編排、證明與說服他人的方式。
文學的再現、替換、隱喻或轉喻讓我們理解某種現實或虛構。但是這樣的方式無法清楚地或完全地在文化之間轉換與翻譯(不可共量或不可翻譯性)。事實上,牛頓與愛因斯坦對於力的思考也是一種不可翻譯的模型。這種自然科學的模型是否只是一套對於自然界再現的寓意,而被以一種實證的方式來操作與證明。牛頓的力學在愛因斯坦中是一種特例的情況,並不是全部的物理場域。但是,我們知道牛頓力學仍然可以有效解釋地球上大部分的物理運動情況。承認牛頓力學是一種部份真實並不是否定他的解釋力與特殊環境的限制。而是我們可以知道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可以使用牛頓力學原理。相同地,透過理解部份真實與田野工作中的權威與不可翻譯性、民族誌書寫時的限制(修辭、拼貼與並置等技巧)時,我們更清楚身處的環境與限制,而理解到知識的獲取時的極限和倫理。
民族誌寫作真的是一個介於之中很有意思的跨學科。既被要求要有科學分析基礎與調查方法的過程,但總歸是寫出來的,這就又涉及文本與表現,因此剛好可說落在科學與文學這兩者的交集(前者不要的東西如虛構、主觀性就落在後者範疇),既然是表達的過程,就會涉及選擇什麼要放進來,甚麼排除掉,而這排除又難免不遭外力影響寫者,因此無論如何所呈現的民族誌,表達的不完全性,即為部分真理/部分真實。當能意會這樣的不完全性,我想作者之間就不需要相互指責,誰寫的才是正確的,而是要能更明白各自的限制,確實所能說出的只有自己所知道的部分。更何況文化是動態發展的,所以在面對成文所述都是一個有限時間於有限年代接觸有限資訊提供者的切片敘述。因而就算以男性為主要涵蓋調查敘事呈現的也是部分真理。體認不完全與不確定。
而在形成寫作他者民族誌的同時也是建構寫作者自我的時候,就像上週葉老師提到的,做研究就是面對自己的提問「你是誰」、「要往哪裡去」。透過參與觀察寫作,其實寫作者也在反思自我。
民族志的書寫不管是獨白式、対話式、複調式或者是互為主體式,都只是話語編排方式的𣎴同,書寫者隱而未宣的寓意或光明正大的反思式言語在其中,我們都要承認民族志的寓言性。這並不是說民族志是虛構的,而是說民族志是在真理對立面這種意義,表達的是所書寫的文化和歷史的不完全性。如果否認,則無異是將自己的生產方式定位在有創造力的文化和歷史變遷之中抽離。多種諷刺也逐漸浮現:將研究主體涷結在過往的時間中、眼見為憑的視覺至上論、單一性別(男)為主體的論述,研究主體不謹能書寫自己的文化也可評民族志書寫者等等更為嚴苛的挑戰出現。例如受訪者腿上的民族志與民族志書寫者來訪前用的是同一本、當訪問受訪者時他\她認為你應該要先去看哪一本書再來訪問,不只人類學家具有知識霸權,研究主體也逐漸具有了。過去民族志的書寫被認為是可以掌握該研究主體的文化且具有權威的書寫,但現在人類學是在一個移動的層面去建構事物,已經不再有一個阿基米德點可從此發現全世界。
這一週的文本,我比較可以理解所為民族誌的fiction的概念,一種在民族學學術紀律與知識權威下的田野文化研究工作的他者報導重寫與他者文化再現。但是,在一般認知上,他者社會文化是隨時與生活環境與文化接觸在變遷,而人類學民族誌的知識論與政治權力關係也一直在調整。在這樣的變遷過程,民族誌的fiction特性還是存在。
但我自己身為本土田野研究的後進者來說,在人類學這樣的學術紀律與知識論,立場已經處在”格格不入”的特殊情境,尤其我們的民族誌書寫要面對”後殖民”之後的”內部殖民”與”自我殖民”的特殊階段與情境,那什麼是在不均等政治與權力關係及制度下的”真實”呢?
我沒有辦法站在中立客觀的位置,來設計田野研究與訪談綱要。我承認我在研究原住民族土地議題的時候,是站在相對於接受現代保留地制度的原住民菁英(參與鄉公所管理者、依法登記比較多土地者、中央主管單位的原住民菁英)的相對位置,來設計我的訪談大綱,以及研究背景動機,乃至於分析理論的採用。我得承認,我的田野並沒有顧慮到支持接受現代國家土地制度的原住民(菁英)的立場。我也承認,我描述的故事其實也是部分的事實。但我只能在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做交代。
其實,我對原住民族土地權利研究及批判保留地制度是殖民遺緒的制度的立場,與其他支持原住民保留地制度的相關研究(土地行政、森林管理、行政管理、法律學系…等研究原住民土地制度歷史與利用的)並不衝突。因為學術的作品公開呈現給所有得讀者,而不同的研究時期與期間的研究結果其實也呈現我們社會對此議題的認知變遷的過程。而重點在於社會知識的發展與變遷過程,是公開與分享,且有反思的語言。而這樣環境下的民族誌書寫都是可以接受或可做公評的;另一方面,研究者與讀者必須有相對的多元尊重的體認(這有一些難)。
這幾週的閱讀讓我對人類學作者反思做為作者過程,有了很粗淺的認識,但是卻對作者這個角色的定位產生懷疑,連帶對於自已可能做為作者的立場,也產生懷疑(我的作品能夠回應這些「部分真實」或是「置身當下」的挑戰嗎?)。以部分真實而言,過去的我也肯定這個概念,但我們總會傾向於去辨識為什麼作者可以去說明有部分真實在裡面(而不是全部都不真實),同樣的社會事實,哪一種可能會較讓讀者信服(或者較不會被反駁),或者所有的文章都可能被安置於部分真實的「自白」的傘下之下,從而避開有關真實性的討論或檢視?在這個時間點上,我不但對做為社會學家的「可能未來」產生失落感,甚而對於過去習慣的生物醫學研究者的角色產生動搖,對於過去生產的知識和現在手邊的研究案,產生立場的動搖。想不到我也體會到了如此「格格不入」的感受,這是好事還是壞事?這是必然還是偶然?
張貼留言